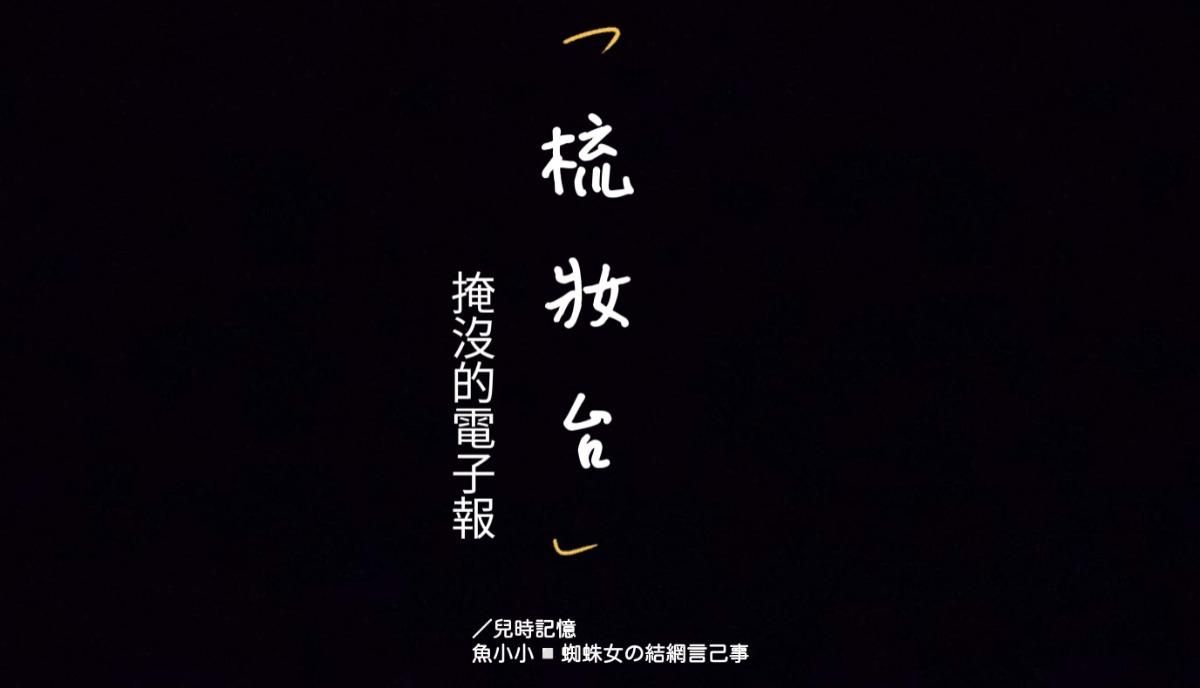幻化成蝴蝶,不問莊生。
除了一時興起,我從不曾
認真思考過這個問題,糊里糊塗
也來來去去九千二百五十九個豔陽陰雨天,往後
仍舊是比天風更輕,更輕。
只是在期待與失望的相互拉扯中無力生還,
選擇以最苟延殘喘的方式,任憑明天一睜開眼
是天還是地,一如不知飄向哪的蒲公英
也不確定是否再一陣風起,將沾染上哪片衣襟。
風,是往哪個方向吹?
這個世界的童話在情歌中不斷搬演,三隻小豬最後
其實也被大野狼吃掉,然而
摩天輪還是轉向天堂一圈又一圈。
而我,依舊任性的要聽兒歌入眠,
嗜戀那最安心的依偎。
漸漸的,不那麼可怕,甚至有些同情誘發的憐惜。
也越來越陷的沉迷在,和那面鬼鏡
談心的午夜時分。
那種黯淡神傷幽幽低吟,那裂嘴的格格詭笑,
儘管很多時候,不得不反駁他的蓄意煽惑
但也必須承認,確實有種蠢蠢欲動
而幾乎無法抵抗的痛麻。
夜貓的眼在漆黑中閃爍待發的
跳踉,無聲卻強烈的暗語。
星火即便燎原,也不過一根菸的時間。
灰燼之後樂聲停舞暫歇,依然潮起潮落
卻戒不掉,迷眩影綽的腳步與孤寂的填補。
初夏的陽光將隨著南風款款流動,在指縫間浮沉。
我仍習慣在自己的夢裡釋放所有的想望,和貪婪
幻化成蝴蝶,不問莊生。
最後我們是不是能左擁右抱是不得而知了,
但至少可以兩倆抽著鴉片,煙裊而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