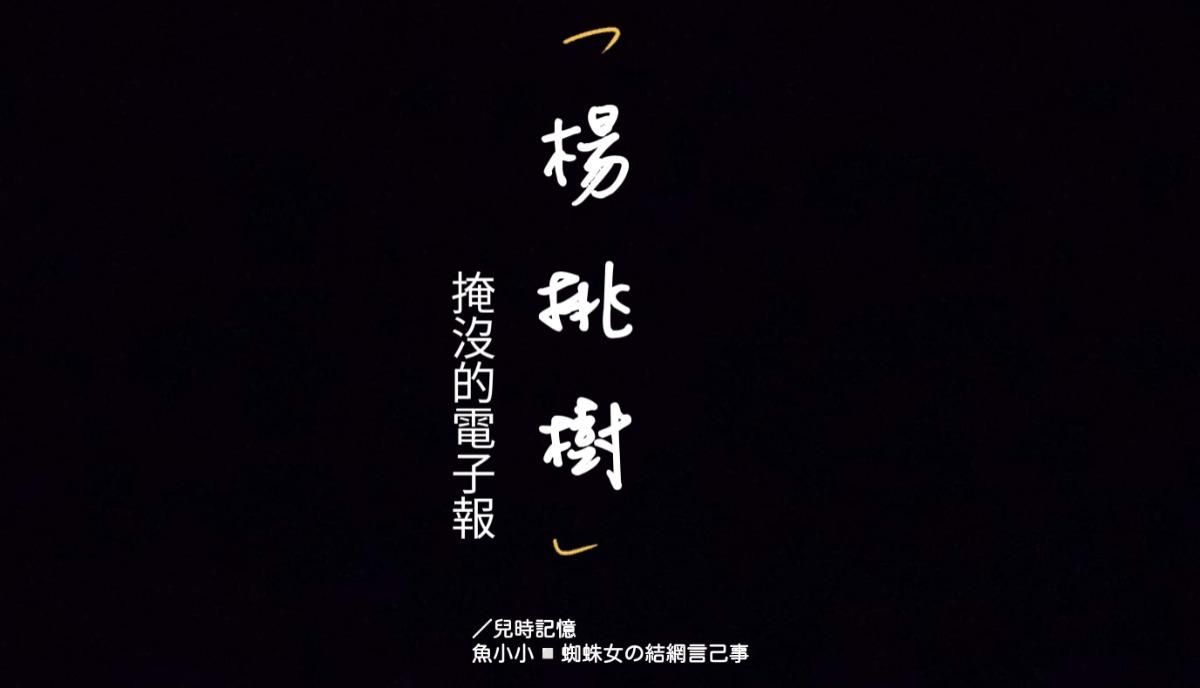17歲時的我,發電子報
──僅此致我最懷念的祖父母
無論人事如何改變,如何牽攣乖隔,我始終堅持相信,儘管相距遙迢,只要往天際望盡,就可以看到椰樹的臉。
從入口處走進來左手邊,老厝的左前方,
楊桃樹的茂密隔離了前一戶鄰家的人事,
只有大人們互有認識。
阿婆的臉很熟悉,可我卻對她很陌生,
玩耍時見她走來,
我們只會忙著跑去喊阿嬤和媽媽。
爸爸說給我們做個鞦韆玩,我的眼睛都亮起來,
瞌睡蟲早就全跑了個精光,跟著爸爸屁股跑。
看東看西,左摸摸右摸摸,不時還使力扳幾下,
看來是選定這枝幹較粗大,而且還有些彎歧的楊桃樹!
爸爸說以前這個地方本來是想種其他果樹的,
想過種仙桃、荔枝,可是種了幾次還是枯死了。
直到後來放棄改種楊桃,也不知是為什麼,
隨隨便便的就這麼大棵了。
「看!長得這麼好,還結實累累!」
爸爸是綁了又釘,釘了再綁,
還要我坐上去盪看看高度如何?
我窩著看,沒一會兒的功夫就完成啦!
這些天來,都得和弟弟搶著玩。
再過幾天就要除夕,媽媽帶著我到美髮院,
說過年都是要燙頭髮的。
好在不是燙我的髮,
小時候的爆炸頭只適合可愛的小娃兒,
那些照片看了都覺得好笑!
美髮院的阿姨抓起我左鬢的頭髮,順著頭頂,
爬了個辮子到右邊的鬢前,
綁了個當時最流行的樣式!
外加繫上一條紅色的緞帶,媽媽滿意的笑了笑,
我更是得意!
爸爸要我和弟弟分別在鞦韆上照張相,
相片裡的我,
長長的頭髮飛得好高好高,笑得好開心好開心!
++後記++
爸爸這趟到南部開會,
比「傳說中的堂姐」早一步回台北。
伯父聽說堂姐的兒子似乎跟我同校同班,
爸爸帶著興奮的表情向我問起。
原來田代的媽媽是我的堂姐,
爸爸說她要叫他叔叔,以前做囝仔的時候,
她和姑姑比較好,後來就到台北去唸書了。
她的老家就是我們老厝前面,
被楊桃樹遮住的那一戶,爸爸說:
以前祖先把笏留給他們,把劍留給了我們。
和田代同班,可之前彼此卻沒說過一句話。
每天看到他都很想跑去告訴他這件事。
親戚散離得這麼廣這麼遠,
沒想到我們竟然可以同校同班,
真的很難叫人相信!
那麼,他應該喊我阿姨囉!原來他早就知道了,
只是二個人這麼生分,遲遲不敢開口。
帶著難掩的期待和幾許情怯。
「媽,讓你跟一個人說說話。」
接過話筒,我不知道她在台北的哪個地方,
可是她的聲音卻這樣緊緊貼著我的耳。
「那時候我在你們班選家長會長的單子上,
看到你爸爸的名字就覺得很熟悉,
雖然同名同姓的人也不少,
可是我就覺得那是他!」
電話的兩頭只有幾句話,卻笑語不斷。
✏️
十七歲時的我,發電子報
──僅此致我最懷念的祖父母
如今看來,許多用字遣詞頗為怪異
敘述上也多不通順,但
我不想作任何修改。
多年之後讀來,才發現
那個連話都講不好的自己
二二六六的也要說這麼多
原來是想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