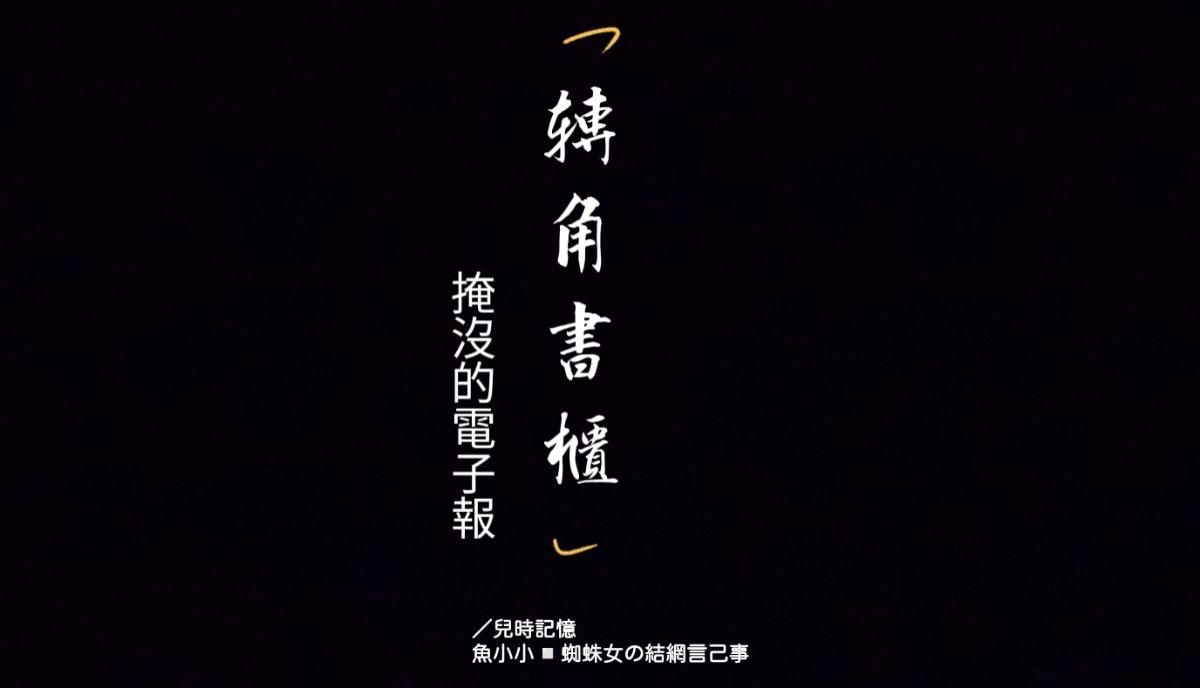一陣風沙後,彷彿被一隻手給掩蓋了。
倒晃幾下,酒壺甩下最後幾滴,大漢不耐煩抿抿嘴,奮力的往地上摔個粉碎。蹲在街道一旁的男人,來回擺動著兩條手臂,赤裸的上身,汗水扒過結實的背。答答的馬蹄闖進了平靜下的忘憂關。白袖底下握著一攏長鞭,白皙的手腕領著一匹棕馬。
男人躡手躡腳的從後頭靠近,突然間向前一撲,羅帕兒振開長鞭,鞭即挺直,一個盤蛇回旋,緊緊勒住男人的頸子,猛力一抽,整個人騰空轉了三兩圈,血水汨汨地自嘴角流出。一群暴賊像饑餓的虎狼般飛撲而上,烏棕馬發狂地蹬起前腳,連連長嘯。隨即長鞭一掃,一排人立刻翻仰倒地。飛蛇調頭,往覆盤旋,舞弄攏擊,羅帕兒的一條手臂好似生了百尺長,上下翻飛。忽地鳴鞭一剉,黃土地瞬即浪湧兩波塵沙,幾個莽漢掩面倒退好幾步,桌面給劈開成了兩半。
胡拓擱下嘴邊一碗水酒,三兩步便貼近,一把將羅帕兒捉住:「跟我走。」遲來的大醫王佛耶律瓦橋正準備出手:「胡拓?」見暴賊不斷的蜂擁,躍身跳起,藉幾個漢子的顱肩飛步追去。
——————————————————
一見耶律瓦橋,胡拓使力地像要嵌進懷中,兩手緊緊地掐著她的背脊。耶律瓦橋細吻連連,嘴唇、鬢髮、耳際,吐著她的鼻息:「胡拓,可有惦著我?」
——————————————————
「拓兒,看我帶了什麼好東西回來!」羅帕兒拎著一隻雞,她收起笑容,轉而原本冰冷肅然的臉:「師姐,妳怎麼會在這兒?」
耶律瓦橋起身披上外衣,向前拉起羅帕兒的手,親睨的笑著說:「近日忘憂關頻傳群暴,師姐擔心帕兒恐遭賊亂。豈知來遲一步,見胡拓將你帶走,就一路跟了過來。帕兒,妳沒事吧?」溫柔的勾起羅帕兒耳鬢的髮。
羅帕兒怔忡,拿開耶律瓦橋的手,偏過頭偷望了拓兒一眼:「師姐,帕兒沒事。」轉身走了出去。
—————————————————–
「忘了胡拓,你我師姐妹一輩子相依相守?」羅帕兒猶豫了起來。
「因為胡拓,傷了妳我十幾年師姐妹的感情?帕兒,夾在妳我之間的男人,該死。」
「即使我倆聯手也未必殺得了他。不過‥他這個人,就是太多情了。」耶律瓦橋將藥瓶反握在羅帕兒的掌中。
「甦心活泉?」羅帕兒詫異地看著師姐。
耶律瓦橋淺淺的一抹笑牽動著嘴角:「死活人,顧名思義形同死人,唯聽覺猶存,其餘盡喪與一般死人別無兩樣。」語罷,數聲狂笑,揚長而去。
—————————————————-
「帕兒,快救救瓦橋吧!她說她沒臉見妳,服毒自盡了。」胡拓抱著耶律瓦橋哭倒在地。羅帕兒趕緊掐了掐師姐的手腕,心裡有了個底。
「胡拓,是你害死了我師姐,一命抵一命!」
胡拓一聽,失魂地攤坐在地。蕭蕭的風聲嗚鳴,振得白袖如笑裡刀,和修長白皙的腿一樣叫人喘息。
羅帕兒振鞭一甩,「帕兒!」胡拓翻個跟斗,閃了過去。
拓兒扶著她,炙熱的吻落在她的頸肩。
憤怒一剉,黃沙倏地揚起。
指尖穿過髮,佔有了耳際。
錯綜盤旋,長鞭的末端不斷地在胡拓的耳邊嘶吼,擊碎不到一寸冷凝的空氣。
突然一個回馬槍,竄逼的盤蛇牢牢鎖住胡拓的頸項,濡濕的額髮,溫熱的肢條,
胡拓廝磨著她的耳鬢,埋進了耶律瓦橋胸前的暖香。
猛力一抽,騰空翻滾,捲起黃沙。
靜靜的,羅帕兒在耶律瓦橋的身旁蹲了下來,臉色出奇的漠然,拔開瓶塞一傾而下,句句寒峭:「死活人,顧名思義形同死人,唯聽覺猶存,其餘盡喪與一般死人別無兩樣。必須在半個時辰內,服下甦心活泉七滴,即可通脈復甦,死人還生。」泉水爬滲的痕跡,在一陣風沙後,彷彿被一隻手給掩蓋了。